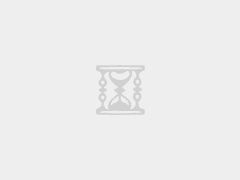我國幅員遼闊,從西到東橫跨東五、東六、東七、東八和東九五個時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全國統一采用首都北京所在的東八時區的區時作為標準時間,稱為北京時間。北京時間是東經120°經線的地方平太陽時,而不是北京的地方平太陽時。北京的地理經度為東經116°21′,因而北京時間與北京地方平太陽時相差約14.5分。北京時間比格林尼治時間(世界時)早8小時,即:北京時間=世界時+8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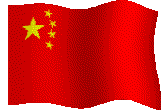
標準北京時間在線校準
|
現在標準北京時間是:
|
電臺里這樣的聲音,我們已經非常熟悉了。北京時間,也是中國人十分熟悉的一個概念。那么,北京時間是怎么來的?要回答這個問題,也許幾句話就夠了。不過要把事情說清楚,那就說來話長了。
晷影漏刻曾用來測時報時
不用很古,大約是一百多年前吧,大多數中國人還是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他們的時間概念,基本上就是看看太陽在天上走到什么位置了,根本不需要有多么精確。
清王朝同治元年(公元 1862 年),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正在領兵與太平軍打仗。他在日記中記過他為家中婦女訂的時間表:
早飯后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食事;
巳、午刻后紡花或績麻衣事;
中飯后做針黹刺繡之類細工;
酉刻(過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縫衣粗工。
曾國藩用的時間單位,還是以在中國社會運行了數千年的傳統的十二時辰來計時的。
以往的時候,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中,官府會敲鼓或擊鐘來向市民宣告時刻的變化,在小一些的城市或街道,值班的更夫用敲梆子來提示時間的演進。聽不到梆子聲,聽聽家里飼養的公雞已經啼叫了幾遍,人們也能大致判斷出時間已經到了哪個時辰。
測量時間的日晷
官府怎么來知道時間呢?他們是通過晷影漏刻來測量的。這樣測出的時間,就是當地太陽運行的時間。據郭慶生先生《中國標準時制考》一文中說,清代的編歷授時工作由欽天監負責,至大清覆滅,他們一直使用晷影漏刻測時報時,這樣測得的時間,當然是北京當地太陽運行的時間,用術語來說,就是北京地方視太陽時,而頒發通行全國的歷書——《御定萬年書》,也是按照北京地方視太陽時計算出來的。
關于時差這個事,也許有人知道,不過對多數老百姓來說,這不重要。因為他們活動的范圍都太小了,活動的速度也太慢了,時差根本影響不到他們的生活。
孫小淳先生在《從“里差”看地球、地理經度概念之傳入中國》一文中考證說,宋、金末年,效力于蒙古帝國朝廷(即后來的元朝)的耶律楚材在他編算的《庚午元歷》中提出了“里差”的概念。里差,其實就是現在我們通常說的時差。
耶律楚材提出“里差”的天文依據是月食觀測。元太祖十五年( 1220 年),耶律楚材隨鐵木真大軍西征,駐留在尋斯干城(即今烏茲別克斯坦的撒馬爾罕)。那一年的夏天,正好發生了一次月食現象。耶律楚材在尋斯干城觀測到的月食開始時刻比在開封早了約 1 更半。由此他認識到,中原地區的“子正”時刻大約相當于尋斯干城的“初更”時刻,進而推演出了“里差”的數值。
不過,耶律楚材提出“里差”,并沒有和地圓及經度概念聯系在一起,后來元明時代的歷法,也沒有考慮“里差”的問題。只是到了明末,西方地圓概念再次傳入中國并被接受,這時的徐光啟才又提到耶律楚材的“里差”概念。
西方工業革命催生時區劃分
對時間測量的精確要求,是伴隨著工業革命的需要產生的。在大象公會《為什么格林威治時間是世界標準時間?》一文中,對西方人劃分時區的做法,有著很有趣的描述。
現代時間標準的建立,離不開準確的鐘表。最早能持續不斷工作的機械鐘,出現在 14 世紀初期歐洲的修道院,以滿足僧侶們準時祈禱的需求。這種鐘十分笨重,只有時針,用整點報時的方式宣布時間。由于精度有限,僧侶每天至少要對時兩次。隨著技術的完善,機械鐘的精確度不斷提高, 1475 年第一次出現“分針”,但直到 1665 年才將時間精確到秒。
中世紀的節奏還體現在地方時上。甚至工業革命初期,各地時間仍然沒有統一標準,散漫隨意的設置仍然普遍。工程師亨利·布什在 1847 年的一本小冊子中寫道:“坎特伯雷,科爾切斯特,劍橋……無數的城鎮,各自有教區時鐘、市場鐘,每個都在宣示其獨特的時間。”
這時,火車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的時間觀。鐵路發展三十年后, 1839 年,出現了第一張火車時刻表。這是一種全新的管理方法,整個流程精確到分鐘。這與中世紀散漫、差異的時間觀迥然不同。
這一時期,另一件重要的發明也誕生了:電報。電報能跨越遙遠的距離即時通訊,使得與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的校對變得準確可行。 1854 年,通過電報線路,格林威治天文臺與東南鐵路站臺相連,能準確地傳遞天文臺時間信號。 1860 年,英國的主要城市都能由電報線接收格林威治的報時信號。
在鐵軌和電報線路大規模建設的幫助下,交通與通信網密集的相連,變得越來越復雜,對時間誤差的容忍度越來越低。鐵路公司開始強硬要求經過的城鎮,都修改為倫敦(格林威治)標準時。一些城市的居民為了交通和電報的方便,發起了“與倫敦時間一致”的請愿活動。
1855 年,不列顛島與愛爾蘭 98% 的公共時鐘調整為格林威治時間。這是第一個將時間統一的國家。
1868 年,新西蘭殖民政府以東經 172 ° 30 ’為準,制定新西蘭全境的標準時。通過電報線路,新西蘭標準時與格林威治標準時相協調,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用經度設定標準時的地區。而這只是一個開始。
1876 年,一個大膽的計劃被加拿大工程師桑福德·弗萊明提出:以格林威治時間為標準,建立東西半球協調一致的 4 個時區。這個提議逐漸被人們接受。最終在 1884 年,經美國提議, 41 個國家參加了華盛頓的國際經度會議,通過了格林威治所在經線為本初子午線, 180 °經線為國際日期變更線,格林威治天文臺時間為標準時,建立全球時區的方案。
時區觀念 19 世紀末傳到中國
從明代起,就開始有外國傳教士將鐘表帶入中國進貢給皇帝。清代時,清廷宮殿里的外國鐘表擺得琳瑯滿目,據說康熙收藏的西洋鐘達 4000 件。但這些時鐘始終也只是皇親貴族們的玩意兒,并未對社會生活產生真正的影響。
自從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后,清政府被迫開放的口岸城市越來越多。上海作為最有代表性和最繁華的開放口岸,也是外國租界最為集中的城市,來往的外國輪船越來越多,進出口貿易日益繁忙,外灘上的海關大樓應運而生。而在這座大樓的樓頂上就鑲有一面西式大鐘,因為來往的船只需要一個統一的標準時間來指揮。
于是在 19 世紀 80 年代,法租界當局在上海外灘建起了一個信號站,在正午時刻利用信號塔頂落球報時,并測風力。它由法國傳教士辦的徐家匯觀象臺來控制,旨在為來往上海港的各國船只服務。
最初,這個氣象信號站用的時間標準是上海本地的“平太陽時”。 1884 年,在華盛頓召開的“國際子午線會議”上,首次確立了在世界范圍內時區的劃分方法。格林威治標準時將整個地球分成了 4 個時區,而中國大部分的繁華地區,即中國的東部沿海地區都在東八區(即以東經 120 度經線的時刻為標準)。大約 19 世紀末,中國的沿海口岸也開始改用格林威治標準時,即東經 120 °的標準時來計時了。當時人們把這個時間標準稱為“海岸時”。
到 1902 年的時候,中國海關就提出以這個“海岸時”作為中國的標準時間。 1902 年,掌管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還是英國人赫德。而制定中國的標準時間這種事情絕對屬于中國政府的主權,由“海關”來制定實在是不合適,于是也只能說得含含糊糊:“海岸時”只在東部的各海關口岸實行,而在其他地區特別是農村內地,“其時區范圍未經規定”。然而,當時的鐵路系統,以及長江一帶經濟繁華地區,顯然也開始實行“海岸時”了。
中國現代鐵路的開創,起始于鴉片戰爭前后。到 1894 年甲午戰爭后,各列強在中國獲得了 1 萬多公里的路權,掀起修鐵路的高潮,到 1911 年,中國已經出現了 9400 公里的鐵路,包括京奉線、京漢線、膠濟線、津浦線、滬寧線等,而經營鐵路是需要標準時間的。
民國時期劃分過五時區
到了民國七年即 1918 年,當時的中央觀象臺提出劃分全國為五個時區:
中原時區:以東經 120 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江蘇、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廣東、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遼寧、黑龍江及內蒙古之東部,可以看出,這個“中原時區”實際就是今天的格林威治時間的東八區,也就是“北京時間”;
隴蜀時區:以東經 105 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陜西、四川、云南、貴州、甘肅東部、寧夏、內蒙古中部、青海等;
回藏時區:以東經 90 度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內蒙古、甘肅、青海及當時的西康西部、新疆及西藏之東部;
昆侖時區:以東經 82 度半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新疆及西藏西部;
長白時區:以東經 127 度半經線之時刻為標準,包括吉林及黑龍江東部。
可以看出,中原時區、隴蜀時區、回藏時區都是整時區,而長白時區、昆侖時區是半時區。
郭慶生在《中國標準時制考》一文中寫道:“今天廣播電臺的六響報時信號和電視臺的時碼顯示畫面,對全國各個角落的普通群眾真是再方便、再熟悉不過了,以致人們很難想象 世紀初要得到比較準確的時間有多么困難。作為中央政府專司測時編歷機構的中央觀象臺,直到消亡竟沒有一臺好一點兒的望遠鏡,沒有無線電收訊機,京畿重地的授時依舊沿用在城墻上施放午炮的古老辦法。”
也正因為如此,這個五時區的方案,除沿海地區外只不過是紙面上的方案。
到 1928 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建立首都,中原標準時的應用也不斷擴展。 1935 年 3 月,交通部令全國電報局一律改用標準時,并令上海無線電報局及南京有線電報局分任每日廣播之事;南京電報局每日 11 點 30 分左右對時一次。海關、電報總局、鐵路局以電報將標準時刻傳遞到各地所屬機構,在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北平等地,車站、碼頭、大銀行、大機關及繁華市區街道,多置有大鐘(時稱標準鐘)為一般市民提供時間服務。
1939 年 3 月 9 日,抗戰中的國民黨政府內政部在重慶召集“標準時間會議”,對以前的五時區方案做了少量修改,并決定于 1939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但同時決定“在抗戰期間,全國一律暫用一種時刻,即以隴蜀時區之時刻為標準”。可以想見,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下,日本占領的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還是在使用“中原時間”。到了抗戰勝利恢復使用中原標準時的時候,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卻仍然使用“隴蜀時”,因此當時人們回憶“滬渝、滬蓉、滬昆等線民航飛機的旅客下機后需撥動手表,進退一小時”。
值得一提的是,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占我國東三省, 1932 年 3 月 1 日成立偽滿洲國,強令在東北使用日本本土采用的東經 135 度標準時。抗戰期間,淪陷區的日偽華北政權也曾試探使用東經 135 度標準時,但最終沒敢這么做,還是使用中華民國正統的中原時。
“北京時間”成標準時間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兩三年內,全國各地所用的時間比較混亂。根據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地球物理所 1952 年編撰出版的《天地年冊》,截止到 1952 年年底,全國至少在理論上仍然實行五時區的舊制,甚至連時區名稱都照舊。
北京時間何時產生?中國科學院國家授時中心高級工程師郭慶生在《建國初期的北京時間》一文中,做過如下考證: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原標準時”稱謂已不合時宜,況且舊政府敗退臺灣后還繼續用此呼號播音報時。新中國廣播報時需要一個色彩鮮明、通俗上口的新名稱,這就為“北京時間”的出世鋪平道路。“北京時間”的問世及隨后取代五時區計時的舊制,是中國近現代時間計量的重大事件。
1949 年 9 月 7 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定都北平,改北平為北京”的決議。同年 10 月 7 日西安人民廣播電臺稱:“本臺時間以北京時間為準”。這是筆者迄今見到的有“北京時間”字樣的最早文獻。所以,“北京時間”第一次出現的日期,可以鎖定在 1949 年 9 月 7 日至 10 月 6 日的 10 天之內。
1949 年 9 月 7 日,“北平”改名為“北京”的同一天,北平新華廣播電臺改名為北京新華廣播電臺。因北平新華廣播電臺隸屬中央,所以其上級主管部門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先行一步,將其更名的同時,一并將廣播報時呼號冠以“北京”稱謂,這是很自然的符合邏輯的事情。所以筆者推斷:“北京時間”的問世當在 1949 年 9 月 7 日。
可能是遵照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的指令,新中國成立后的各地方廣播電臺很快將自己的節目時間改為中央臺使用的北京時間,以表示和中央一致。原屬隴蜀時區的地方政府陸續聲明采用北京時間。 1949 年 11 月 日,西安市政府通知:“本府征求各方意見,為與全國各主要地區時間一致,自本月三日起,停止使用隴蜀時間,改用北京時間。”成都市 1949 年 12 月 7 日解放,也在其后十余天內宣布使用北京時間。 1950 年初,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短短幾個月內,全國各地除新疆、西藏外,實際上全都采用北京時間為統一的時間標準。而現在,我國新疆地區會同時使用烏魯木齊時間(東經 90 度標準時)和北京時間兩種標準。
值得指出的是,經過郭慶生考證,初期使用的“北京時間”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北京時間,也就是說它不是標準時,而是北京地方的視太陽時。當然,很快“北京時間”就采用了東經 120 度的標準時間了。
-

包月鮮花 每周一花 一月4束鮮花套餐
價格范圍:¥55.0 至 ¥2,298.0 選擇選項 本產品有多種變體。 可在產品頁面上選擇這些選項 -

小清新花束 青春與活力鮮花花藝
價格范圍:¥169.0 至 ¥599.0 選擇選項 本產品有多種變體。 可在產品頁面上選擇這些選項 -

特色花藝 干花花束 人民幣花束 婚禮花藝
¥99.0 加入購物車 -

花束花籃 新款高檔開業花籃 創意喬遷花籃
價格范圍:¥299.0 至 ¥1,188.0 選擇選項 本產品有多種變體。 可在產品頁面上選擇這些選項
 春暖花開
春暖花開